



当一个社会急匆匆往前赶路的时候,不能因为要往前走,就忽视那个被你撞倒的人。——贾樟柯
1997年,山西汾阳。一个忧伤的年轻人在街头游荡。
他沉默、隐忍,经常抽烟、独行,望着人来人往,一言不发。
他在这破旧的小城里寻找金钱,寻找爱情,寻找希望,最终一无所有。
他的名字,叫小武。
当一个社会急匆匆往前赶路的时候,不能因为要往前走,就忽视那个被你撞倒的人。——贾樟柯
1997年,山西汾阳。一个忧伤的年轻人在街头游荡。
他沉默、隐忍,经常抽烟、独行,望着人来人往,一言不发。
他在这破旧的小城里寻找金钱,寻找爱情,寻找希望,最终一无所有。
他的名字,叫小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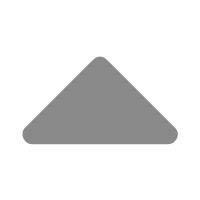 9414
941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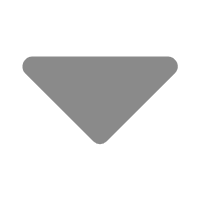 353
353



“故乡”——贾樟柯电影中最令我迷恋的颜色与母题。
我与贾樟柯电影的狭路相逢,还在大学时代。那时候我在广院(今天的传媒大学)读电视新闻,学纪录片。那一年林旭东老师做了一个讲座,我鬼使神差地跑去听。在讲座上,林旭东老师放了贾樟柯的《小山回家》,一部纪录片色彩浓厚的短片,那粗粝凝视的画面令我久久无法忘怀。
多少年后,我才理解了“回家”二字在贾樟柯电影中那份沉甸甸的重量。
“故乡”——贾樟柯电影中最令我迷恋的颜色与母题。
我与贾樟柯电影的狭路相逢,还在大学时代。那时候我在广院(今天的传媒大学)读电视新闻,学纪录片。那一年林旭东老师做了一个讲座,我鬼使神差地跑去听。在讲座上,林旭东老师放了贾樟柯的《小山回家》,一部纪录片色彩浓厚的短片,那粗粝凝视的画面令我久久无法忘怀。
多少年后,我才理解了“回家”二字在贾樟柯电影中那份沉甸甸的重量。
紧随其后我看了《小武》,完全爱上了这部电影。《小武》的故事发生在贾樟柯的“家”,汾阳县城,那个距离我南方的故乡接近2000公里的地方,但我却在《小武》中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故乡,那个东南一隅的海边县城,仿佛看到我成长的县城中的人和事,那份心有戚戚焉的慨然和触动,实在美妙。
究竟是什么东西打通了南与北,连接了时空,让一个80后的我,在一个70年代生人拍摄的电影中找回了自己的记忆?
《小武》上映20年后,2018年,我回到故乡,在家中重看了这部电影,终于拾到了答案。
《小武》故事发生的90年代末期,正是我成长的岁月。那是改革开放后的20年,《小武》之于我,有点儿像《站台》之于贾樟柯,是成长的痕迹。汾阳一如我的家乡,虽只是局促的县城,却是整个社会变革与冲撞下的缩影。
不同于大城市的庞杂和分散,县城的人际关系紧密,人际关系的变迁和冲突显得尤为突出明显。贾樟柯曾说过《小武》的原名是《靳小勇的朋友,胡梅梅的傍家,梁长友的儿子,小武》,那是一个靠人物关系设置层层推进但又近乎各自独立的三段式叙事。虽则贾樟柯说他三段式叙事的源头是《无用》,但其实在《小武》中他的叙事偏好已经初见端倪,他习惯用多角度去刻画主体,或是为了追求一种全面性和复杂性。而在《小武》中,这种多维角度则源自小武周边的人际关系。
有趣的是,《小武》故事的一开头,靳小勇这个人物并非直接出场,他的名字第一次被提及,是从小武和靳小勇共同的朋友“更胜”口出道出,而小武得知靳小勇要结婚,则是来自被他唤作“郝老师”的老警察。《小武》写的是小武,侧面却写出了一副关系紧密的县城群像。而令我觉得亲切的是,这些近乎妯娌的县城关系中透露出了一种我所熟悉的、小地方的那份浓厚的人情,就像老警察与小武,虽然身份完全对立,却呈现了一种难得的熟悉和亲和,小武唤老警察作“老师”,老警察也完全待他如同晚辈一般,在“警察”身份的严苛之外也还有一份宽容和爱护。
这种人情,非但唤起了我的县城记忆,某种程度上,竟然也令我想起了幼时对于“港片”的印象。是的,看《小武》,我有种强烈的感觉,像是在看一部香港电影。90年代,我的观影哺乳,完全来自于香港电影。香港电影中除了热衷表现邻里的亲和与人情,也经常呈现出一种武侠式的情义与情怀。而《小武》中,恰好两者兼备。小武这个人物,就像武侠小说中的草莽一般,虽身份卑微,却有着一股执拗的、对于情义义无反顾的坚守。所以当《小武》中响彻出录像厅中吴宇森电影的对白时,实在令我有些不谋而合的兴奋。而小武的“武”字,也很难不令我产生诸如“武侠”一般的联想。
正因为有情有义,所以在变革之中就更显得怆然,那是武侠小说中的“悲壮”,是英雄人物的时不我与。贾樟柯的电影始终贯彻着一个命题,是时代的变革与个体情感的冲撞,是社会极速发展所带来的高度物质化和阶级分化,令情感产生的迷茫与无所适从。《小武》中最令我难忘的一场戏,是小武去找靳小勇,当他把红包交给靳小勇,靳小勇却不要,将红包扔回给他,那个红包恰好掉在小武翘起的二郎腿上。那场戏是一个长镜头,当红包落在小武的腿上时,那一刻的小武实在令我心酸、心疼,他是那么尴尬、不堪,却仍要努力维护着自己的自尊、维系着那份执拗,那是我最欣赏的一段王宏伟的演出,因为他表现出了那场戏的残酷,也正因为残酷,看出那个人物内在无比的深情、孤独与哀伤。
20年后的2018年,改革开放的40周年,我们的故事和20年前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只是愈演愈烈。变革来得越来越快,个体的命运在时代之中有若微尘,更多的情感在物化的年代中不知何去何从。在我南方的故乡中,那份感受更加深刻而真切,阶层分化和贫富悬殊令越来越多的情感关系渐渐疏离。回头再看《小武》,并未觉得是20年前的电影,因为那些命题,那些冲撞,在此时此刻依然成立,依然照进现实。
而贾樟柯的可贵之处不止是纪录了变革时代中的无奈和迷惘,更重要的是他用电影纪录下了在时代变革之中个体情感的珍贵。纵然面对变化的猝不及防,有着山河依旧人面全非的感伤,但个体的生命力永远是充沛的,情感永远是人最重要的依托。就像在贾樟柯电影中无处不在的流行曲,都象征了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最朴实纯粹的个人情感。只要旋律一响起,就会令人泛起记忆,想起最弥足珍贵的回忆与感情,就像《小武》里的《心雨》《给爱丽丝》,就像《山河故人》里赵涛伴着《go west》再次起舞,脸上带着百般情愫的复杂笑容。
题外话,回到故乡,其实我的父母还给我讲了一段往事,原来东南一隅的他们与山西也有过交集,那却是我从未知晓的他们的历史。1987年,我两岁,那时我父亲有好朋友在太原承包了一段铁路工程,便拉上了当时生活尚算窘迫的我的父母。当年有那么多北方人南下谋生,那时我的父母却为了生活出走山西。母亲说她和父亲坐了足足38个小时烧煤的火车硬座从南方来到了太原,火车上人群摩肩擦踵,到了太原他们已经精疲力尽。工程进行了两三年,他们和那位朋友耗费心力,却到底没有赚到什么钱,后来也再没有什么来往了。
不知道父亲的那位朋友现在怎么样?他们是不是还会回忆起那些在太原一起的日子?他们中有那么多小武,那么多靳小勇,都在飞速变化中疏远、消散了。但在父亲口中提起,只说“那时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而我只记得父亲常哼唱刘欢的《少年壮志不言愁》,而那是1987年的电视剧《便衣警察》里的一首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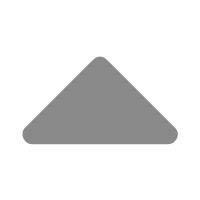 9176
917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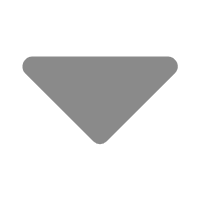 2454
24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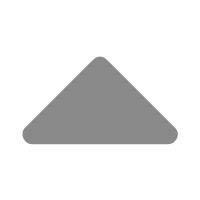 6312
6312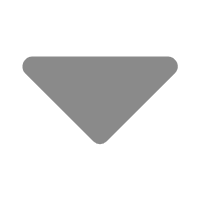 2525
2525



每一个三线城市,都会有小武这样的人。他们年轻时是混世魔王,不管是打架还是偷窃,总有一手让人羡慕的手艺,能在同龄人中靠混子的痞气风光一时。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混世魔王身边曾经的小弟,个个转身投入社会洪流中,有钱的有钱,有势的有势,曾经倜傥的混混们则沦为小偷小摸的犯罪分子,曾经的浪子不得不变成了今日穷苦的孤家寡人。小武怪不得朋友。是他自己不适应时代。当别人在权钱交易的灰色地带扑腾时,他还在乡间公
每一个三线城市,都会有小武这样的人。他们年轻时是混世魔王,不管是打架还是偷窃,总有一手让人羡慕的手艺,能在同龄人中靠混子的痞气风光一时。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混世魔王身边曾经的小弟,个个转身投入社会洪流中,有钱的有钱,有势的有势,曾经倜傥的混混们则沦为小偷小摸的犯罪分子,曾经的浪子不得不变成了今日穷苦的孤家寡人。小武怪不得朋友。是他自己不适应时代。当别人在权钱交易的灰色地带扑腾时,他还在乡间公交车上偷窃农民的钱。他把偷窃当作事业,幼稚的同时,又如守卫着传统手艺人尊严的末路困兽一般惹人同情。他整天领着一帮孩子到处游走,曾经的小弟结婚请柬都发到了警察手里,却到不了小武手中。他拿六斤人民币换不来朋友一个笑脸,因为一个小偷不会给朋友带来任何实际帮助。这是一个早就不讲人情的时代,这个时代讲究利益。对大环境,小武没有抵抗的能力。他执拗的相信友谊天长地久,相信爱情海枯石烂。他一个人在无人的澡堂吼叫时,空空的回音是对他执拗最好的回答。这样一个活在过去的人,没有现世那漠然的冷酷,取而代之的是古朴的真诚和善意,它温暖着小武,也温暖着活在现世的每一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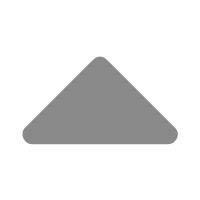 6003
600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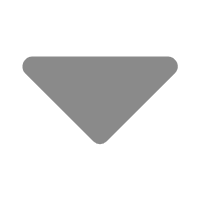 486
4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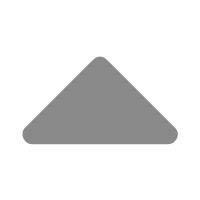 5901
590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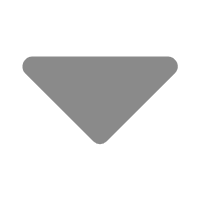 2653
26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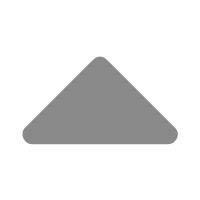 5760
576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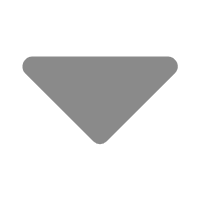 29928
299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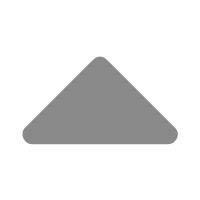 2177
217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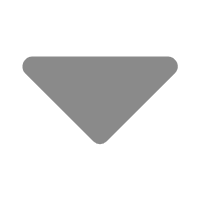 1561
15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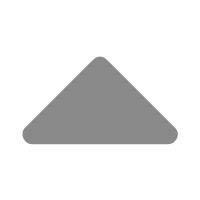 1960
196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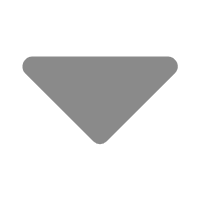 1447
1447



表导演基础课上老师在黑板上用下定义的方式写了几句话。比如,自由是好的,爱情是伟大的,男人是不可信的,女人是善良的。尊严是珍贵的。然后他给我们放了小武。影片的一开头是一段滑腻的二人传,充满肉欲的气息。其中男人的声音酷似赵本山,或者干脆可能就是赵本山。老师算的上是贾樟柯的拥趸。他神情激动的指出开端这段二人转的重大意义,贾樟柯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走的多么前无古人。我从来没有听过赵本山这样的段子,如果
表导演基础课上老师在黑板上用下定义的方式写了几句话。比如,自由是好的,爱情是伟大的,男人是不可信的,女人是善良的。尊严是珍贵的。然后他给我们放了小武。影片的一开头是一段滑腻的二人传,充满肉欲的气息。其中男人的声音酷似赵本山,或者干脆可能就是赵本山。老师算的上是贾樟柯的拥趸。他神情激动的指出开端这段二人转的重大意义,贾樟柯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走的多么前无古人。我从来没有听过赵本山这样的段子,如果不是贾樟柯,我不知道赵本山从前竟然也说这么荤的东西。老师说,现在赵本山当老板了,开公司了,这种东西他以后也不会再说了。但是多么精辟啊,一听这种东西我们就好像可以回到那个时候似的。昆德拉说,无产阶级是粗俗的,资产阶级是媚俗的。这句话大概可以在这得到印证,从无产到有产,赵本山再也不会说那些黄色二人转了,他脱离了粗俗,也与过去一刀两断。同样与过去一刀两断的还有靳小勇,他开了公司,上了电视,娶了个比倪萍还好看的新媳妇,大宴亲朋,转眼成了汾阳县上有脸面的人。朱元璋年少时有个患难的伙伴,落魄时大概也掏心掏肺的对别人说过苟富贵,勿相忘之类的话,到他富贵的时候,伙伴便不知好歹的真的找过来,提起他从前窘迫的经历,朱元璋让人把他拉下去砍了。靳小勇的情形与此也大致相同。一旦功成名就,尊严好像顷刻就高头大马起来,满身都散发着圣洁的光,不容亵渎。要摆脱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去,就要与那些不上台面的朋友划清界限,分清立场。梁小武显然属于要被划清的那类。于是他就被划分了,连曾经管他们的民警都拿到了大红的帖子,他记得六斤钱的誓约,却被人家当臭氧或者臭鸡蛋一样规避了。小武觉得很难受,除了感到友情上的失落外,他的自尊心也受到了深深的伤害。这个时候老师问了一个问题,在贾樟柯看来,小武的尊严可不可以被践踏。我们犹豫了一会稀稀拉拉的说不行,老师感到很满意,影片继续,胡梅梅走远又折回来在小武脸上干脆的亲了一下,小武感到一阵窘迫。他体味到了从来没有触及过的感情范围。他把一侧腮帮子鼓起来,又收回去,嘴里像装了个大桃核,整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老师又停了下来,他说,这是饱含深意的一吻,小武在这一吻里体味了对他来说从未有过的女性温柔,还获得了珍贵的尊严。尊严是珍贵的,因为他生而有之。老师说。个人尊严,边缘化人的尊严也值得维护。但是显然,值得维护并不代表可以真正受到维护,有地位的靳小勇的尊严显然更容得到保障。纵然我看来,就某些方面,比如偷了钱包又把身份证塞到邮箱里(那个年代身份证对人身份的确定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牢记着最贫困时和靳小勇的六斤之约,梁小武要比靳小勇更有道德感。靳小勇告别了过去,他从小偷转向了大偷。贩烟不叫走私叫贸易,开歌舞厅不叫搞色情叫发展娱乐业,他成了有脸面的人,尊严是不是在温饱后的衍生品。靳小勇的尊严是不是比梁小武的尊严更高贵?大二的时候看《唐人街》,说偷一块钱是偷,偷一百万反而会成为人民的表率。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这个世界是怎样的生存法则呢?老师接着让我们做填空,这是一个( )的社会。这是一个成功至上的社会。是什么模糊了人们的是非观和价值感。这是社会的发展么?还是发展的社会解放了人的天性。那些我们自古被谆谆教导而形成的观念是否真的是正确的呢?比如谦虚,比如勤勉。社会以一个吊诡的方式决定着谁是他的宠儿。究竟什么是这个社会的成功法则呢?真正完全处在弱势处在被审查地位的“梁小武”是没有机会和能力表达自己,审视自己的。有话语权的人则早已脱离了弱势的状态。如果你刚好平庸平凡弱势,那么你该如何在这个社会上自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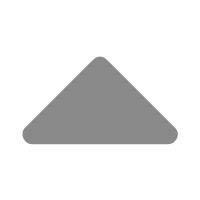 1562
1562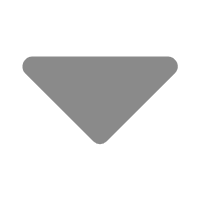 1465
14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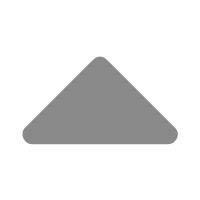 1347
134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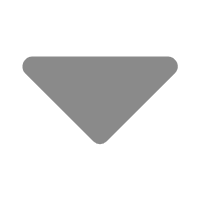 717
717



有酒方能意识流贾樟柯拍完《小武》后,约我出来见面的人突然多了起来。我自不敢怠慢,也不想错过任何一个人。江湖上讲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象我这种拎一只箱子来北京找活路的人,突然得到别人的注意,总是心生感激。阅人胜于阅景,况且那时穷有时间,即使只是扯淡闲聊也乐于奉陪。见面就要有地方,这对我是一个难题。那时我还没有办公室,家小,杂乱也不可待客。每次约会我都让对方定地
有酒方能意识流贾樟柯拍完《小武》后,约我出来见面的人突然多了起来。我自不敢怠慢,也不想错过任何一个人。江湖上讲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象我这种拎一只箱子来北京找活路的人,突然得到别人的注意,总是心生感激。阅人胜于阅景,况且那时穷有时间,即使只是扯淡闲聊也乐于奉陪。见面就要有地方,这对我是一个难题。那时我还没有办公室,家小,杂乱也不可待客。每次约会我都让对方定地方。客人又都客气,说要将就我。于是沉默一下,动一番脑筋,说出来的还是三个字:黄亭子。直到今天我的活动范围还都在新马泰一带,新是新街口,马是马甸,泰是北太平庄。这些地方离电影学院近,上四年学习惯了,腿便自己往这边跑。黄亭子在电影学院北边一百米,是家酒吧,全称叫黄亭子五十号,因为隔街可见儿童电影制片厂,好找。下午客稀,也便于说话。那时,不远处的北航大排挡正是黄金时代。入夜时分,三教九流蜂拥而至。烟熏火燎中有孜然的香味,就着红焖羊肉可以看见械斗。那边新疆大叔用维汉双语招徕四川小姐,一低头身边这桌大学生不知为什么已经哭成一团。这里混乱,迷茫但充满生机,对我的口味。但黄亭子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每次从北航回学校路过这里,透过窗口看见里面灯光昏暗,便觉无味。山西家穷,从小父母就节约用电,15瓦的灯泡暗淡太久,让我日后酷爱光明。也是青春不解风情,那时心中充满宏大叙事,自觉很难融入烛光灯影。第一次进黄亭子是97年初,我在香港碰见摄影师余力为,两人打算日后合力拍戏。我剧本还没写,他已经来了北京。接他电话时,他在黄亭子里等。进了黄亭子,他的桌上已经有了几个空酒瓶。我点上一支都宝,这烟别名点儿背。但一切如此幸运,这次见面让我们决定一起去山西看看,这便有了日后的《小武》。小余能喝,成了黄亭子的常客,我便常来,与老板成了好友,时间长了有人戏称黄亭子是我的办公室。老板简宁是诗人,开酒吧也开诗会,常在午夜时分强迫小陈和他下象棋。小陈是调酒师,见我进来总喊贾哥,并让莉莉倒茶。莉莉是服务员,简宁的远亲,爱看电视,常梳一头小辫,把自己打扮成民国戏中的女子。这样我在北京又多了一个去处,即使无人相随,来了黄亭子也总能找到人聊天儿。象我这样的人不少,有一个英国人叫戴维,在化工学院作外教,他总是准时晚上十二点来酒吧,要一杯扎啤,仰着脖子一边看足球一边和小陈聊他伦敦乡下的事。这些思乡的面孔在午夜时交错,彼此没有太多交情,所以能讲一些真实的话题。我还是习惯下午在黄亭子见人:约朋友举杯叙旧,找仇家拍桌子翻脸,接受采访,说服制片,恳求帮助,找高人指点。酒喝不多话可不少,我的家乡汾阳产汾酒,常有名人题词。猛然想起不知谁的一句诗:有酒方能意识流,大块文章乐未休。于是又多了一些心理活动。在推杯换盏时心里猛的一沉,知道正事未办,于是悲从心起。话突然少了,爬在桌子上看烛光跳动,耳边喧闹渐渐抽象,有《海上花》的意境。于是想起年华老去,自己也过上了混日子的生活。感觉生命轻浮肉身沉重。象一个老男人般突然古怪地离席,于回家的黑暗中恍惚看到童年往事。知道自己有些醉意,便对司机师傅说:有酒方能意识流。师傅见多了,不会有回应,知道天亮后此人便又会醒:向人陪笑,与人握手,全然不知自己曾如此局促,丑态百出。到了下午,又在等人。客人迟迟不来,心境亦然没有了先前的躁动,配合下午清闲的气氛,站起来向窗外望。外面的人们在白太阳下骑车奔忙,不知在追逐什么样的际遇。心感苍生如雀,竟然有些忧伤。突然进来一位中年女子,点一杯酒又让小陈放张信哲的歌,歌声未起,哭声先出。原来这酒吧也是可以哭的地方。现在再去黄亭子,酒吧已经拆了,变成了土堆。这是一个比喻,一切皆可化尘而去。于是不得不抓紧电影,不为不朽,只为此中可以落泪。over电影看多了以后,开始有一个判断电影好坏自己的标准。我喜欢动机很纯的导演世道艰难
不为不朽,只为此中可以落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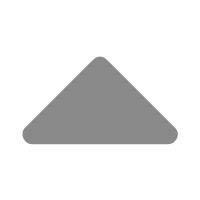 1312
1312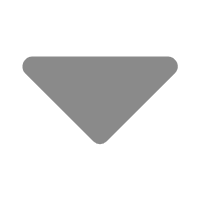 1617
1617



不久前终于看了贾樟柯的《小武》,看的时候一个恍惚,觉着自己又到了那个不大不小的县城,像是喊着我的名字,我大街小巷的奔突着,身后的灰尘飞扬成不可名妆的模样,额头上的汗水成了一种多余的发泄。是啊,年轻的小伙子们,在一个学校里,除了荷尔蒙分泌,就只剩下汗水分泌了。当然,那时候,年轻的小伙子压根不知道是什么在不断的远去。有一天我们毕业,咣当的一声,哦,是我们的青春在远去,不断的远去。可是已经迟了。那
不久前终于看了贾樟柯的《小武》,看的时候一个恍惚,觉着自己又到了那个不大不小的县城,像是喊着我的名字,我大街小巷的奔突着,身后的灰尘飞扬成不可名妆的模样,额头上的汗水成了一种多余的发泄。是啊,年轻的小伙子们,在一个学校里,除了荷尔蒙分泌,就只剩下汗水分泌了。当然,那时候,年轻的小伙子压根不知道是什么在不断的远去。有一天我们毕业,咣当的一声,哦,是我们的青春在远去,不断的远去。可是已经迟了。那时候的我们精力旺盛非凡,你知道,这样的形容词尽管有些夸张,可是你却可以想见,一群年轻、精力旺盛的小伙子们,在尘土飞扬的县城里到处飞奔的场景,那是何其的壮烈。是的,我说的是那首歌:《霸王别姬》。屠洪刚在喇叭里唱得荡气回肠,谁也不知道,喇叭里的前一首歌里还放着小虎队充满奶气的声音:.....你的心我的心结成一个同心圆.....。我们完全不顾及什么突兀以及虚假,那些刚刚还在聊聊我我的男女生们,猛然间有了一种壮烈、凛冽于心间,站在食堂里敲起饭碗,叮叮当当:"我站在,猎猎风中,剑在手......"仿佛食堂外面就是乌江,那三楼的教室就是战场。在歌声中有人匆忙奔走,埋头不闻耳边的呼喊以及壮烈,直至将一个女生的饭碗撞倒在地上。然后,有人唱一句,"问天下谁是英雄"。这完全不合拍的事情屡屡发生----这本该是多么美好的青春的啊,作家、教育家、科学家们都在叫喊----然而就在这懵懂以及机械中,转眼即逝。这世界是荒唐而合理的存在。小武与那个陪唱的小姐梅梅在唱着《心雨》----这首在中国大地上流行许久的爱情歌曲。贾樟柯以一首湿漉漉的歌来让我们知道,小武的爱情确实存在过。他像那时候的我们一样,与一个女人(我们的年代是女生)压马路,唱歌----这是小县城的爱情存在的普遍方式。小武不善于表达自己的内心,他只是抽烟,给女人关心,不停的找女人玩。而那时候的我们,只是学得很嚣张,让我们的情感像一场电影那样充满神奇而美好。然而我们失去了成年人的耐心,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们莫名的行为,成就了一出可笑的闹剧。我们还是做不到那么多的美好倾注于这段时光。我们渴望的美好,在一个本该可以美好的年岁,被我们生生的错过,转瞬消逝。那时候我喜欢上了行走----或者说,是喜欢上了四处走走。周末的时候,我们穿上白色的球鞋、运动服,在那个县城四处奔突。我们雄赳赳的追上并超越两辆并行的自行车----那上面坐着一对疑似恋人的年轻男女学生,然后在转弯的地方慢下来大口呼吸着,捂住不停要奔突而出的心脏,那自行车上的少女啊,她怎知我们对她谈论已久?我们在县城居民诧异的目光中自鸣得意的奔跑着,或者,他们很久没见过奔跑的少年了吧。当然,他们也可能怀疑我们是神经病。我们与县城的生活秩序不符,因此我们要被注视、忽视、蔑视。穿过附近的民居的时候,我们忽然想唱起那首歌:爱江山更爱美人。我们最喜欢那一句:那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我们没有江山美人,我们有很多的教辅和试卷,我们都不愿孤单。那个我们喜欢的姑娘,就像那个梅梅一样,后来不知去了何方,没跟我们说再见。那段我们奔跑过的路,据说已被钢筋水泥覆盖。我们走了,那些见证我们成长过的东西正在往后退去,往后隐去,往后逝去。小武的生活里有台球、电影院(或者录像厅)、卡拉OK厅。那时候的我们,去得最多的是前二者。在台球厅里,染发的少年抽着烟,很臭屁的学着港台明星的扮相,喇叭裤,中分头。在录像厅门口,我们被耸人听闻的影片名吸引,那些影片名里蕴涵着:性、暧昧、武打。一个当街的喇叭清晰的传递着录像厅里的配音击打着我们稚嫩的耳膜,我们热血沸扬起来,像是唱着那首《霸王别姬》的那样激越,血脉顿时到了任督二脉。这样的生活在记忆里显得真实而荒诞。那是当时的我们么?记忆里曾帮忙同桌写过情书,向那位漂亮的姑娘许一个今生今世。诺言写在花绿的信纸里,在当时的我们看来,显得馨香而美好。后来这样的情节随风而去,我们迎风而长。小武生活在"市场经济大潮"里,许多人翘首期盼能过上新的好的生活。"改革开放"像一阵风吹过,万物复苏然而诸如小武这样县城小民,却是难以受益。这样的情节随时上演,随风而去。这是多么不相合的两个比喻,却都显得如此的不真实。我们后来逃出了县城,到了城市,到了一个更为荒诞的所在,我们美其名曰:发展。可是那个小武,锁在电线杆上的小武,用舌头顶在腮帮子上,他是反抗还是忍受?他毫无办法的,要过着县城里荒唐而平常的生活。像一头行走在沙漠里的骆驼,被绑在一根突如其来的电线杆上,看着满目的荒凉,看一切生活发生、消逝,又继续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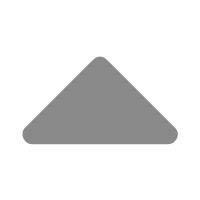 1165
116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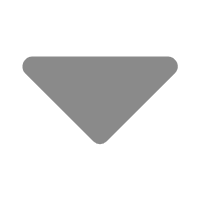 1906
19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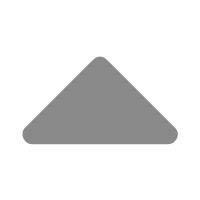 1120
112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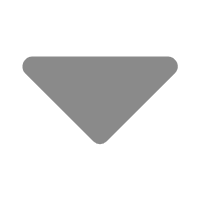 994
9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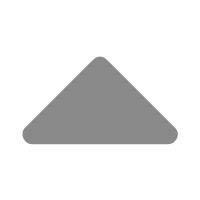 1098
109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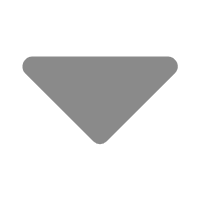 2567
25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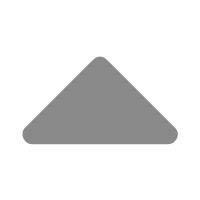 1075
107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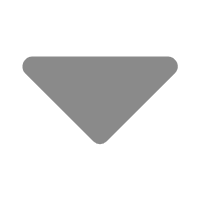 188
1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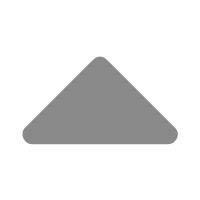 1046
104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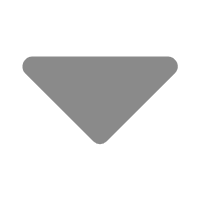 1720
17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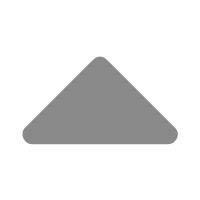 1045
104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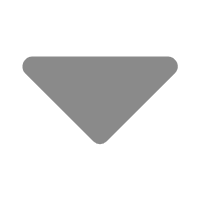 4653
46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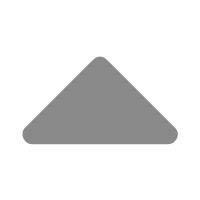 1004
100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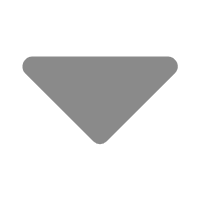 180
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