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雄本色》的影史经典地位不用多加说明,多加论证,任何媒体搞的影史经典香港电影排行榜,《英雄本色》都是不可或缺的电影。芭蕾舞式的纵情暴力场面,周润发戴墨镜、叼火柴、穿大衣的造型,义薄云天的兄弟豪情是几代华人影迷甚至亚洲影迷的经典回忆。有很长一段时间,《英雄本色》对大陆影迷来说,几乎定义了香港电影的一切。对于信奉“情怀大过天”的影迷来说,这几乎是一部不容置疑的电影圣经。
批评的声音当然存在,而且不乏来自香港本土。罗卡就认为吴宇森“感性偏激狭隘,有时不免于为文而造情”,李焯桃的观点则是,“吴宇森的激情动作片我们往往也吃不消,西方的类型片迷却看得兴高采烈,正因为如此心无旁骛地相信类型的西片已难得一见。”
不加节制地宣泄情感几乎是对吴宇森电影的集中性批评意见。《英雄本色》也正是这样一部风格化到极致的电影。罗卡“为文而造情”的批评意见相当中肯,但吴宇森此风格缺陷并非其个人独有,其实是中国电影风格类型的重要传统──苦情戏的遗风。苦情戏是深受“影戏”传统影响的早期中国电影极端重要的一种类型,《黑籍冤魂》、《渔光曲》、《暴雨梨花》、《桃李劫》、《新女性》这些当年深受观众膜拜的电影无不都是让影院观众浸透了悲苦体验的催泪苦情大戏。是非、善恩、爱恨、褒贬、黑白一定要分明,表现方式一定要夸张刺激,初始和最终的落脚点都必须围绕道德冲突(苦情戏本质上都是道德伦理剧)。这是苦情戏最鲜明的艺术特征。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一切人伦之冲突都可以成为苦情戏渲染的对象,要义便是让整体的情境处于悲苦之中。而这种悲苦达致的效果与西方悲剧的崇高感则有本质区别,苦情戏无关命运的荒谬与绝对,无关深度意义的追问,更无视理性精神对于无限世界的把握与探求。所以即便在当年,郑正秋就早已指出苦情戏的艺术幼稚问题,但是要吸引观众也似乎别无他法,“中国看影戏的,大半不耐寻思……刺激愈多、愈受欢迎,这一点,取材的先生们就要用心思了,既不能太残忍,又不能少刺激。”蔡楚生则进一步强调,“在描写手法上加强每一件事态的刺激成分,和采取一些中国特点的刺激素材。”所以要说东西方对比,苦情戏倒是更接近于道格拉斯·瑟克式的催泪通俗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搭错车》、《妈妈再爱我一次》、《法内情》、《唐山大地震》这些在两岸创造了巨额票房的电影其实都属于苦情戏的范畴。
曾经是邵氏片场出身,执导过粤语戏曲片《帝女花》的吴宇森,对苦情戏的成功要义了然于胸。《英雄本色》极端渲染的是兄弟与朋友之间的情义。比较重要的渲染手法是对比(这也是苦情戏的常规手法),由强烈的对比来刺激观众的情绪。宋子豪的性格隐忍,杰仔的性格冲动外放。宋子豪一直默默承受,杰仔一直挑衅攻击。更重要的对比来自情义的强弱。宋子豪与Mark哥之间浩气长存的友情义气,宋子豪与杰仔充满误会与矛盾的兄弟情。为了突出宋子豪与mark哥情义的撼天动地,杰仔在影片中甚至被处理成了相对负面的角色。这也是影片激发观众强烈情绪反应的杀手锏。
好人蒙冤,弱者受欺也是苦情戏主角的一大重要类型。一心悔过苦求给予重新开始机会的宋子豪,却得不到弟弟杰仔的原谅,这关系设置大体符合蒙冤的类型。宋子豪与mark哥还具有强度很高的受虐倾向,面对铺天盖地的责难与暴力,二人有着强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忍受力。这其实也是苦情戏主角的一大特色。
影片中的对比手法不仅表现在性格设置,还体现在大量的情节设置。开场不久之后,就出现了平行蒙太奇。一边是宋子豪在狱中的落魄场景,另一边是杰仔在警队意气风发训练的场景。最重磅的反差对比来自mark哥。当年的意气风发,后来却落魄成瘸子,擦车谋生。昔日稚嫩的小弟阿成,却成为了大佬,对之动辄打骂。这种巨大的反差手法,也是比较容易刺激观众的手法,当然这并不高明,看多了则觉得有点廉价。类似脚踩香蕉片滑一跤引发的喜剧效果。
最夸张的渲染来自暴力。按照吴宇森自己的说法,“不少人看到人家捱打,情感会得到宣泄。”《英雄本色》中的暴力场景有铺天盖地之势,mark哥屡屡处于血肉模糊的状态,吴宇森还酷爱用慢镜表现身体与脸庞受攻击后扭曲的细微运动姿态。可以说,《英雄本色》整部电影的情感几乎都处在宣泄的状态,吴宇森曾说斯科塞斯是“他长期的偶像”,从这一点来看,二人是完全一致。不过在处理情节方面,二人却有重大根本的不同。我们对于一部以歌唱为主的戏曲片,可以忽略其情节的含糊不合理,因为巨大的假定性本是戏曲片成立的前提。但《英雄本色》毕竟是一部在1986年公映的现代警匪动作片,如果我们完全忽视情节的不合理之处,是否对电影的要求太低?《英雄本色》“为文而造情”的后果是留下了犹如马蜂窝一般密集的剧情漏洞。
宋子豪不论身姿谈吐行为,都不像是黑帮社团的大佬。犯罪团伙和黑帮团伙可不完全是一回事。即便是后来阿成上位后,影片对于香港黑帮的表现也过于浮夸,这当然是那个年代香港电影的通病(讽刺的是,香港黑帮社团后来反而开始模仿影片中人物的打扮)。一直到杜琪峰的黑帮片出现,香港电影的黑帮影像才提升到一个新的具有丰富意涵的层次。
前文说道的对比手法,太多缺乏合理性。mark哥腿瘸之后,为何非要给阿成打下手?打的下手也不过是擦车这种最低级的工作。更进一步说,mark哥一直说三年来一直等一个机会,可是这与给阿成打下手有何必然因果关系么?阿成为何又要设计陷害杰仔还要开枪打伤他?他的目的难道不是要利用他为自己的罪行开脱么?阿成继而还痛殴mark哥,此又是异常壮观的暴力场景,慢镜头表现器官喷血,可是这又有何必要?看不出来痛殴mark哥有何目的。仅仅是为了表现阿成的恶,或者是mark哥的不堪,那就纯粹还是为了宣泄而宣泄。一些细部的情节处理更是自我矛盾。阿成派人砸出租车行。宋子豪劝大家不要动手,一动手就又便回罪犯了。结果劝完他人,他自己却反而大打出手,车行老板又用同样的话劝了宋子豪一遍。这简直是哭笑不得的滑稽场面。杰仔拿到了犯罪证据电脑光盘,并不想着立刻上交,严重缺乏基本的职业训练。宋子豪把电脑光盘交给了杰仔后,却又莫名地告诉了他自己要和阿成决战的地点。如果为弟弟着想,这不纯粹画蛇添足?影片的第一场暴力戏,即父亲被杀,就显得过于夸张。杀手居然头撞破玻璃,脸部被滚烫热水烫,身体被刀插入,还有能量反扑,实在不可思议。这场面也只能理解为暴力的渲染。声音部分最不可忍的是主题曲《当年情》(曲风亦是偏向悲苦),几十遍地反复放,在视主题曲重要性很高的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影坛,也很少有这种播放密度。
表演方面对于苦情戏的一大助力来自宋子豪的扮演者狄龙。本就是张彻大弟子的狄龙,表演方法是最典型不过的戏曲风,这当然同其长期浸淫在邵氏武侠片中的经验脱不了干系。狄龙的巅峰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邵氏的没落,狄龙的星途也渐渐不振。在出演《英雄本色》之前,狄龙已经告别巨星地位。《英雄本色》让狄龙重回大众视线。在《英雄本色》中,吴宇森重用狄龙,出演了宋子豪这一角色。他在整部电影中的表演方式,想必是与影片整体的苦情戏风格所要求的。苦情戏很容易导致演员的表演风格导向戏曲风,戏曲风便是程式性、写意性、象征性、假定性、舞台性。演员更多的是要塑造所扮演的角色类型共通的一面,即符号化的一面,而不是演员自我迥异于其他演员的个性化一面。放大一点说,这是早期中国电影演员表演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即便是在《小城之春》这样的所谓经典之作中,也存在着这一问题。戏曲演员所在的舞台空间与电影演员所在的银幕空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加调整的原样复制,效果必然走样,也必然为现代观众所淘汰。好莱坞电影与日本电影在有声电影诞生之初就解决了这一问题。周润发与张国荣在本片中的表演风格便与狄龙完全不一致,二人虽扮演角色的性格大相径庭,却都能做到相对真实化的自然流露。《英雄本色》让狄龙人气大热,但之后他的星途并未有本质改观。倒是狄龙当年的黄金搭档姜大卫,在继承了邵氏风格的TVB电视荧屏上,至少保持住了表演生命。
《英雄本色》最令人矛盾之处,是影片用了最现代的美式镜头语言(如波德维尔所总结),叙事形式却是最陈腐的“影戏”传统之苦情戏模式,强调的母题是家庭破碎后的重建、手足之情的修复以及朋友情义的张扬,大体不脱宣扬忠孝节义的传统儒家伦理内涵。问题在于罔顾剧情基本逻辑的一味渲染儒家之道,一味的宣泄暴力情感,这当真算是超越时代的经典之作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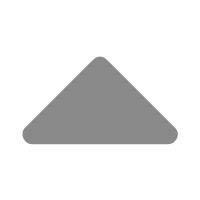 9705
970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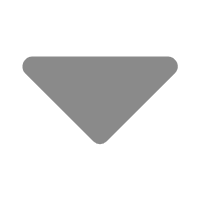 3462
3462